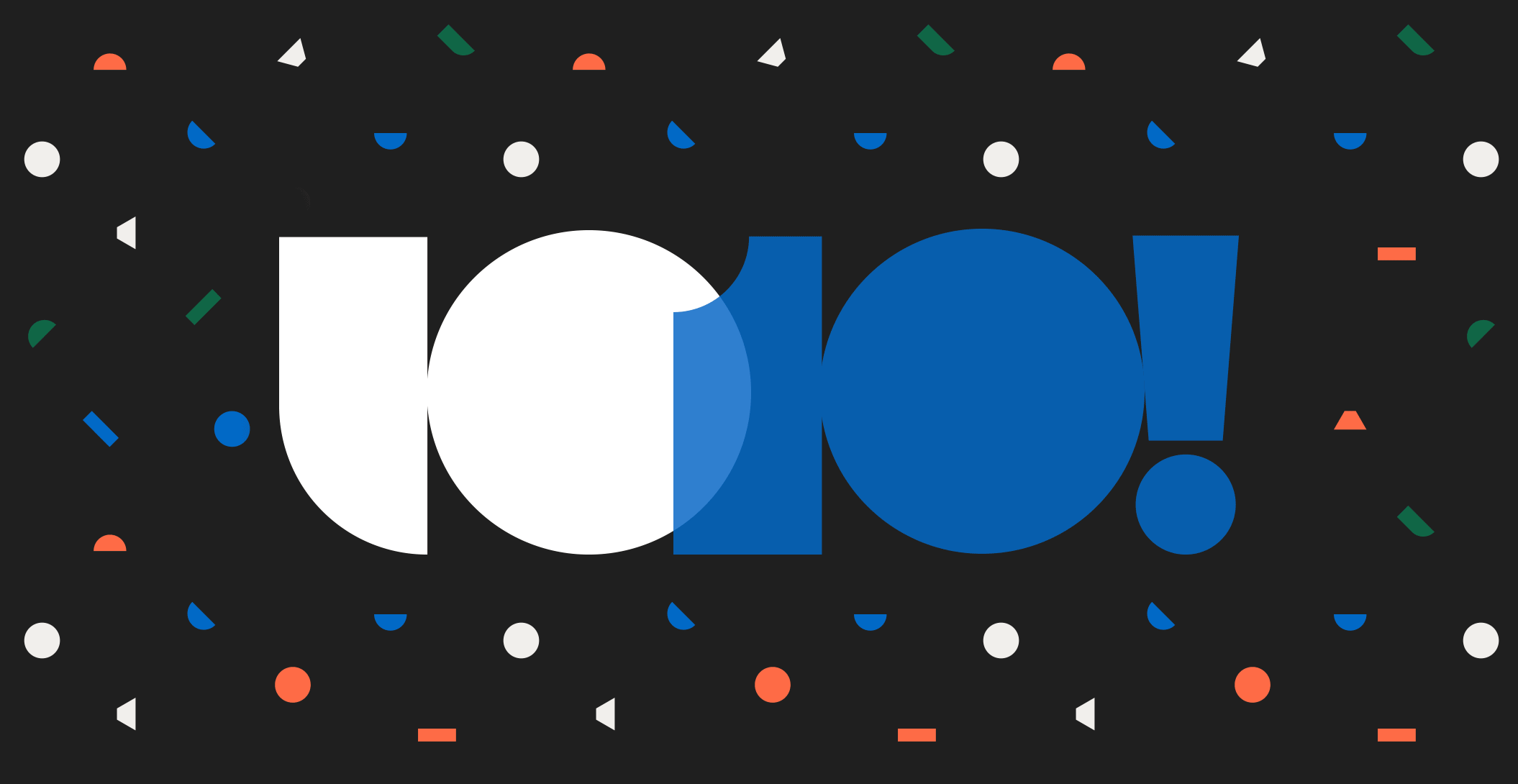
We are celebrating 15 years — and counting — of stories that are deeply researched and deeply felt, that build a historical record of what the city has been.
We are celebrating 15 years — and counting — of stories that are deeply researched and deeply felt, that build a historical record of what the city has been.
To read “What’s in a Gateway” in English, click here.
欢迎点击此处阅读这篇文章的简体中文版本
中文翻譯:劉凱儀、楊伯、張坤雅
沒有牌坊的唐人街算什麼唐人街呢?常被用作劃定世界各地唐人街的邊界,這些影射著傳統中式設計的牌坊無疑與唐人街緊密相連。這個關聯部分原因在於文化融合的演變,另部分在於商業營造。在曼哈頓的華埠,牌坊的顯著缺少並不是意味著缺少一個拍照的機會,而是意味著數百萬美元的社區投資被錯過了。最近一次嘗試塑造一個呈現出華埠的複雜、不斷蛻變的文化和社區的雕塑以失敗告終。現在,一項新的計劃正在進行,旨在重新設計劉錦中尉廣場(Kimlau Square),並在此創建一個「華埠迎客之門」。為了促進社區對話,並闡明關於華埠文化表徵的辯論,建築歷史學家和規劃師Kerri Culhane與心目華埠的總監兼創始人鄺海音(Yin Kong)共同策劃了展覽《地方創生與維護- 華埠的人、地方和文化表徵》,展覽將持續到2024年11月8日。 (心目華埠是紐約市經濟發展公司(NYCEDC)的《通達華埠》項目的建築設計顧問Marvel Architects的社區合作夥伴)。她們在下面探討了牌坊在過去與現在、居民與遊客、文化與商業、象徵與刻板印象的交集中的地位。她們認為,只有一種能夠調和社區多重維度的過程,才能開闢出一條新的前進道路。
華埠到底在哪裡呢?它的定義捉摸不定,因人而異。 不過這塊區域總會有些具象或抽象的痕迹,讓你感覺到,我已經到了華埠。這裡有些建築帶著中式風格的設計,但大多數的公寓樓則為過去一波波移民社區的遺留物。華埠的特色更多地體現在我們如何使用這些空間以及我們在這些空間里如何與彼此互動。這種特色滲透於眾多具有文化意義企業的中文標誌、公園裡的文化及社交活動,以及我們使用人行道的方式:堅尼路(Canal Street)、茂比利街(Mulberry Street)和科西廣場(Forsyth Plaza)上那一排排五顏六色的蔬果攤; 勿街(Mott Street)上中式地方特產店裡頭滿溢而出的乾貨; 格蘭街(Grand Street)上阿姨們販售盆栽、手摘銀杏果及粽子。 這些由社區自發實踐的地方維護(placekeeping),都展現著由社區共同創造的繁華生態系統。
其他視覺上的線索可能包括公共空間設備的設計,如燈籠形狀的街燈,種植竹子的廣場和公園。這些被城市規劃專家稱為地方創生或地方營造(placemaking)的方案,有時是由市政部門根據本地團體或組織的建議來進行。不論是地方創生還是地方維護,每一種方式都為塑造社區的外觀、氛圍和可識別性起著重要作用。因此,所有人都可以在這塊區域獲得一種強烈的區域感,無論你是華埠的社會、文化和政治生活的一部分,還是路過的紐約同胞或遊客。
2021 年,在面臨著911事件造成經濟破壞的第二十年,同時在新冠病毒疫情肆虐的背景下,現任總統將此次疫情歸咎於所謂「中國病毒」,由此觸發了一系列的反亞暴力事件。正值此時,華埠獲得了紐約州政府提供的2,000 萬美元的市中心復興計劃(Downtown Revitalization Initiative,DRI)撥款,以投資於「其作為文化目的地的歷史,以保護和恢復該社區成為一個充滿活力的市中心區域」。 DRI收到的提案中包括設計建造一座華埠門道, 通過這種地方營造的手段刺激旅遊業發展。提案包括了一張援引Wikimedia Commons的照片作為紐約門道的示例,照片拍的是費城華埠的友誼門。這座異彩紛呈的傳統拱門由中國大陸在1984年捐贈。這種將費城的拱門複製一份到紐約華埠暗示著一種可互換的無地方性、並給一個充滿社區特色,區域感的地方帶來可替代的感覺。
紐約市經濟發展公司(NYCEDC)負責管理此項多機構、多組織的項目(後來被稱為《通達華埠》),故意在信息中沒有規定「迎客之門」的外觀;他們將聘請一位藝術家,並通過實行社區參與的過程制定設計。儘管如此,「門道」一詞具有非常特殊的涵義。 牌坊或牌樓,又稱唐人街大門、門道或友誼拱門,源起於神聖的佛教建築。異彩紛呈、裝飾華麗,非常上鏡。不難理解為什麼它們可以促進一個區域的旅遊業,但這些建築早在 Instagram 和社交媒體出現的幾千年前就已佇立於世。這種以印度宗教建築為基礎的古老形式,是如何成為許多華埠的門道的呢?
牌坊,或稱牌樓,是中式空間組織的八個主要特徵之一, 這種建築在漢朝(公元前202年-公元220年)中葉,經由絲綢之路與佛教一同從印度傳入中國。在中國,牌樓傳統意義上的紀念功能與其印度起源類似:將神與非神區隔開來,或是向有社會地位的人士、親屬、學者及遺孀表示敬意。牌坊有地方標記的功能,譬如用於劃定北京各區的邊界的牌坊。
在 20 世紀的過程中,牌坊的意義發生了變化,從舊金山到新加坡,牌坊變成了唐人街的標誌性視覺符號。 搜索「唐人街」相關的圖片,你就能在數頁的結果中看到五顏六色的牌坊。這些自成一體,裝飾華麗的建築,成為華人聚居區的地標;而在類似華盛頓特區的牌坊,卻反襯出了華人社區日漸消散的現象。被人認為中華文化象徵的牌坊深受歡迎,甚至被當今的中國重新引回了北京以提升遊客的體驗。這種現象被Anne-Marie Broudehoux 稱為「唐人街化的北京」。 [1]宗教神聖建築是如何變成了自拍照背景的呢?
三藩市 1906 年後興建的華埠,其散布著塔的商業區,被認為是北美第一個有意商業化的華埠。在地震和火災摧毀了原有的社區後,美國華裔企業家圍繞「美麗的遠東藝術幻想」[2] 重建了三藩市的華埠。他們緊緊接上僅兩年前在1904年聖路易斯世界博覽會裡深受歡迎的中國村。這個中國村在摩天輪和其他有趣的娛樂設施的背景下展示了傳統中國建築。當時面臨著要被趕出華埠的危局,本地華人從中國村取得靈感,將建築環境異域化以吸引白人遊客,這使華人得以留在唐人街,並從此建立了遊客對其他地方華埠的景觀期望。這種巧妙的文化商品化為北美華埠的發展定下了模板,使其成為依賴銷售商業化傳統的旅遊目的地。用歷史學家 Mae Ngai 的話,這是 「排華時代美國華人可利用的少數商業活動領域之一」。 [3]
《通達華埠》項目的範圍包括一個尚未明確,未設計的「華埠迎客之門」。「迎客」這個詞暗示著目標受眾是前來華埠的外來者。考慮到華埠被許多不同華裔和亞裔僑民群體認為文化家園,這個門道如何能為他們服務?它能否滿足多個群體的需求?這樣的門道又應該是什麼樣的呢?「這個門道是為誰而設?」這個問題實際上是一個更大且更複雜討論的問題,其核心在於「華埠是為誰存在?」。 如民俗學家 Winston Kyan 所稱,華埠處於「個人文化與公共消費文化」[4]的交匯處或模糊邊界。它既是華裔僑民及更廣泛的亞裔美國社群的經濟飛地,也是文化家園,然而其一部分小企業自歷史以來嚴重依賴旅遊經濟。在它150多年歷史的大部分,華埠常常被大眾誤解為與中國等同的或是一個位於紐約市中心的異域外國殖民地。華埠的「東方化」雖然在美國華裔缺乏經濟機會的時代催生了一個蓬勃發展的旅遊經濟,不過也造成了對華埠的普遍誤解,這種誤解延伸到了任何具有亞洲血統的人。即便是第五代華裔美國人,仍然可能被問到:「你們到底是從哪裡來的?」。
每一代對自己的華裔及亞裔美國人身份各有不相同的認識。華埠與整個城市之間的關係和認識也隨著歲月的推移而變化。自1965年以來,移民的多樣性和人數的增加使得華埠具有細緻的區域性特徵——從最初以廣府移民為主的華埠逐漸擴展至包含更廣泛的僑民社群,如今這裡每天都有不少於七種漢語及方言被使用。與此同時,隨著亞裔美國人群體的日益富裕,華埠經濟也正在逐步擺脫對旅遊的依賴,以滿足此廣泛群體的需求。如今,一個強大的區域經濟正在為當地居民以及尋求與文化建立更深關係的亞裔僑民提供服務與支持。
孕育了亞裔美國人運動的1960年代的人們,不懈努力爭取了歷史上缺乏的亞裔群體代表性和可見性,以推翻諸如「模範少數族裔」、陳查理和雜碎等為了讓非亞裔美國人更願意接受而簡化的亞裔表現形式。如今,華人僑民社群的代際、階層和文化多樣性挑戰著本質化或東方化的文化表現。儘管如此,世界各地的唐人街中仍存在一些熟悉的標誌:如牌坊、龍和燈籠。同樣標誌對我們社群的不同細分群體中具有各異的象徵意義——可能引發文化自豪感、被刻板印象化的感覺,或毫無意義。關於牌坊及其他「族裔象徵化」的討論,景觀建築師 Chuo Li 指出:「族裔紀念碑的創建往往會將華埠轉變為一個“主題公園”,一個演制文化生產和消費的場所」。[4]在這種說法中,牌坊是為華埠以外的人群所樹立的象徵,而非為居住和工作於其中的人樹立,因而被稱為「迎客之門」。社會學家 Jan Lin 指出,「遊客注視」對華埠的影響使得華裔美國居民為了滿足外來者的偷窺的心理進行適應,並逐漸內化了針對遊客的象徵。 [5] 門道通常借鑒想象中的歷史來迎合這種遊客注視;而我們希望看到的地方營造的策略聚焦在確保華埠未來能繼續地作為一個充滿活力的亞裔美國人文化家園。這種「迎客之門」能如何反映出華埠的社交與文化生活的多樣性?它能否幫助維持社區的生機?
整個社區都同意:當華埠作為文化家園的表現和自豪感都至關重要。多數人民心中所渴望的,但無法用城市規劃的術語來表達的,即是良好的地方營造與地方守護。然而,在缺乏相關廣泛詞彙的情況下,牌坊成為了中國文化的速寫,往往成為通用的默認選擇。我們有機會設計出能服務於華埠的創意公共空間和藝術作品,從而塑造社區群體的敘事,影響其來講述自身的哪些故事以及影響外界敘述我們的哪些故事。華埠所需的「門道」,一個能夠幫助建立跨代的社會與文化聯繫的門道,可能不會以牌坊的形式呈現而出。
社區參與這個工作是必要的、是充滿挑戰的,並且幾乎總是顯得不夠充分的。參與公共會議的人群往往是自我選擇的群體。現實是,無非進行了多種語言宣傳和引導,大多數新移民,尤其是那些剛剛從中國大陸抵達的人,並未參與公共事務。不止缺乏針對新移民們語言上和文化方面的特定宣傳,較新的移民也個人缺乏公共事務的經驗,繁重的工作和家庭責任往往使他們沒有閑暇時間參加公共會議。許多「社區」反饋來自向來參與的積極分子和長期居民們,而他們僅代表華埠和華裔美國社群中的一小部分。有效的參與需要考慮更多視角,這就需要理解複雜的社會環境,並通過多種形式和場所對參與者進行宣傳與溝通。真正有意義的參與需要適應的文化能力:不僅用當地的語言和方言,並要設計出一個讓人們感到舒適的參與過程。
說了那麼多關於門道的話,我們務必反思在紐約修建門道的多次嘗試,儘管只有一座成功修成,別的都未有結果。
美國華裔退伍軍人忠烈坊(1959-62年)
儘管常常被忽視,紐約市擁有美國唐人街中最早的門道之一,僅次於洛杉磯:美國華裔退伍軍人忠烈坊(1959-62年),位於劉錦中尉廣場/且林士果廣場(Kimlau/Chatham Square)。美國退伍軍人會紀念劉錦中尉一二九一分會委託華裔設計師李錦沛(Poy G. Lee, AIA)設計這座牌樓以紀念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犧牲的華裔士兵。這一莊嚴的「新中式」紀念碑履行了牌樓的傳統功能:紀念高地位人物。在遵循文化傳統的同時,美國華裔退伍軍人忠烈坊也反映其時代的現代主義形式,從而成為一項發自華埠社群,並服務於華埠社群的尤為卓越社區紀念碑。2021年,紐約市將這座牌樓劃定為歷史文物,成為了紐約市唯一一座反映華裔歷史與經歷的市立文物。
然而李設計師其實設計了兩份方案。最初的設計是一個宏偉、傳統精美的牌樓,中文媒體描述其方案為「美麗」和「精描細繪」。[6]由於擔心華麗的牌樓將在繁忙的且林士果廣場(Chatham Square)中吸引太多遊客,並分散司機注意力,李設計師被要求製作一個簡化版——一個顯然不是用於吸引遊客的版本。於是,李設計師的詮釋採用了此形式的神聖意義,再加上其時代的風格, 從而設計了一座紀念並弘揚社區的一段重要歷史的牌樓。
紐約華埠的門道 (1982, 2006, 2016-19年)
雖然紐約華埠是美國唯一一個沒有刻板化的牌坊式門道的大型華人社區,但這並不意味著沒有努力爭取過。 1982年,華埠領袖們提出了一項由廣東工程師兼設計師何鐵基(Ho Tieh-Chi )(1937年-)設計的20×40英尺的精美華埠門樓方案,被市政府正式駁回。 2005年-2006年,紐約市議會向華埠的社群及商業團體提供配套資金,以助建起「一座以混凝土與花崗岩門樓,以象徵華埠的入口」。香港出生的 Peter Poon 建築師設計了這個方案,其設想是要橫跨堅尼路(Canal Street),然而市交通局(DOT)拒絕提供相應許可證。
最近一次嘗試建造門道應對所有參與當前的努力的人被視為一篇警示故事。2016年,交通局(DOT)與 Van Alen Institute 和華埠共同發展機構(CPLDC)合作,使用了911事件後劃撥於經濟復興的資金,發起了《唐人街之道》門道設計競賽,吸引競標。此項目的設計大綱從本地社群中徵詢極少意見,卻共收到80多份來自世界各地藝術家及設計師的投標。這些投標中包括了各種刻板元素諸如筷子、美式中餐外賣盒、燈籠、月亮門等,同時也有幾份現代設計感的牌坊。 (為了全面起見,作者們也提交了一份投標。該投標沒有針對推出任何特定的設計,而是圍繞著一個社區參與的方案。)華埠公眾沒有任何機會查看或對80多份參賽作品發表意見;他們只能查看少許設計師自願公布的那些競標,而且只有在線搜索時才能查到。
《龍吟》,由紐約公司 LEVENBETTS 與 UAP 以及澳大利亞籍華裔藝術家李林迪(Lindy Lee)共同設計的方案,最終以匿名評選委員會被選為中標方案。其「門道」主體抽象,佇立在細細的柱子上,由金屬圓柱體不規則地堆疊而成,並且設計了圓柱體有如瑞士芝士般的孔洞。投標方稱他們從苗族鼓樓那裡獲取靈感,然而這種文化淵源卻與紐約華埠的移民史並無直接聯繫。
中標的提案由一個完全白人的設計團隊向第三社區委員會的交通小組委員會介紹提案。華埠社群的成員提出了諸多異議:設計並沒有考慮到風水(作品的孔洞將社區的財運溜走)、設計未能捕捉紐約華埠的「真實」地氣、有些成員希望看到更加傳統的元素(龍、鳳、塔),有些則希望完全超越傳統(不包含金色、紅色,不包含龍)、設計與華埠居民並無關係,並不能起到實質作用、方案並沒有能通過設計帶動解決堅尼路(Canal Street)的行人及行車交通問題。雖然區民在社區會議中以多種原因反對了中標的方案,然而參與者沒有對華埠門道的應當設計達成一致。
面對著社區的反對,交通局撤回了該項目。雖然這無疑讓付出心血的設計師感到失望,但更令人失望的是華埠失去了數百萬美元的投資。如果從一開始就讓社區參與對話,並進行具有適應語言能力和文化的交流,那麼一個滿足社區需求的門道項目或許已經在修建中了。
正如一個迎客之門劃定內與外、唐人街與城市之間的邊界,它也將這些地方連接在一起。實行迎客之門是一個彌合老一代、年輕一代、以及僑民各個角落之間的文化鴻溝的起點,從而讓我們組織社區的宗旨不僅僅基於我們的複雜且常被誤解或抨擊的歷史,而是我們共同的未來。華埠迎客之門將對紐約華埠的認知產生世代影響。我們不對這個新門道假設任何形式——甚至它應否形成實物的形式我們都沒有斷定結論——而是相信信息共享和深入傾聽的過程能夠激發並為社區帶來一個適當的結果。
Anne-Marie Broudehoux, “The Chinatownization of Beijing: Urban Renewal and the Commodification of Identity,” conference abstract from “Identity, Tradition and Built Form: The Role of Culture in Development and Planning: Fif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December 14-17, 1996, Berkeley, California: Traditional Dwellings and Settlements Review, Vol. 8, No. 1 (Fall 1996), 58.
Look Tin Eli, “Our Oriental City,” (1910), quoted in Philip P. Choy, The Architecture of San Francisco Chinatown (San Francisco: Chinese Historical Society, 2008), 18.
Mae M. Ngai, “Transnationalism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Other’: Response to the Presidential Address,” American Quarterly, Vol. 57, No. 1 (March 2005): 59-65.
Chuo Li, “Chinatown and Urban Redevelopment: A Spatial Narrative of Race, Identity, and Urban Politics 1950–2000,”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2011: 214.
Jan Lin. Reconstructing Chinatown: Ethnic Enclaves and Global Chang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8: 172.
联合日报 (United Journal), May 1961.
The views expressed here are those of the authors only and do not reflect the position of The Architectural League of New York.

![[左圖] 公元1世紀的托拉納門,位於印度中央邦桑吉窣堵坡。Leon Meerson 攝影,取自 <a href=https://www.flickr.com/photos/lenchik/116887771/in/photostream/>Flickr</a>。](https://urbanomnibus.net/wp-content/uploads/sites/2/2024/10/07_116887771_9df620592f_o-1536x2048-1.jpg)
![[右圖] 在陝西一座漢朝立的牌樓展現了中國最早對於托拉納門的一種詮釋。俄羅斯前往中國的科學商業遠征,1874-75年。照片取自 <a href=https://www.loc.gov/%20%20item/2021669674/>Library of Congress</a>。](https://urbanomnibus.net/wp-content/uploads/sites/2/2024/10/08_116887771_9df620592f_o-1536x2048-1.jpg)
![[右圖] 中國村,聖路易斯世界博覽會的官方紀念品,1904年。圖案取自 <a href=https://mohistory.org/collections/item/N20408>Missouri Historical Society</a>。](https://urbanomnibus.net/wp-content/uploads/sites/2/2024/10/10_default-e1727873311680-1.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