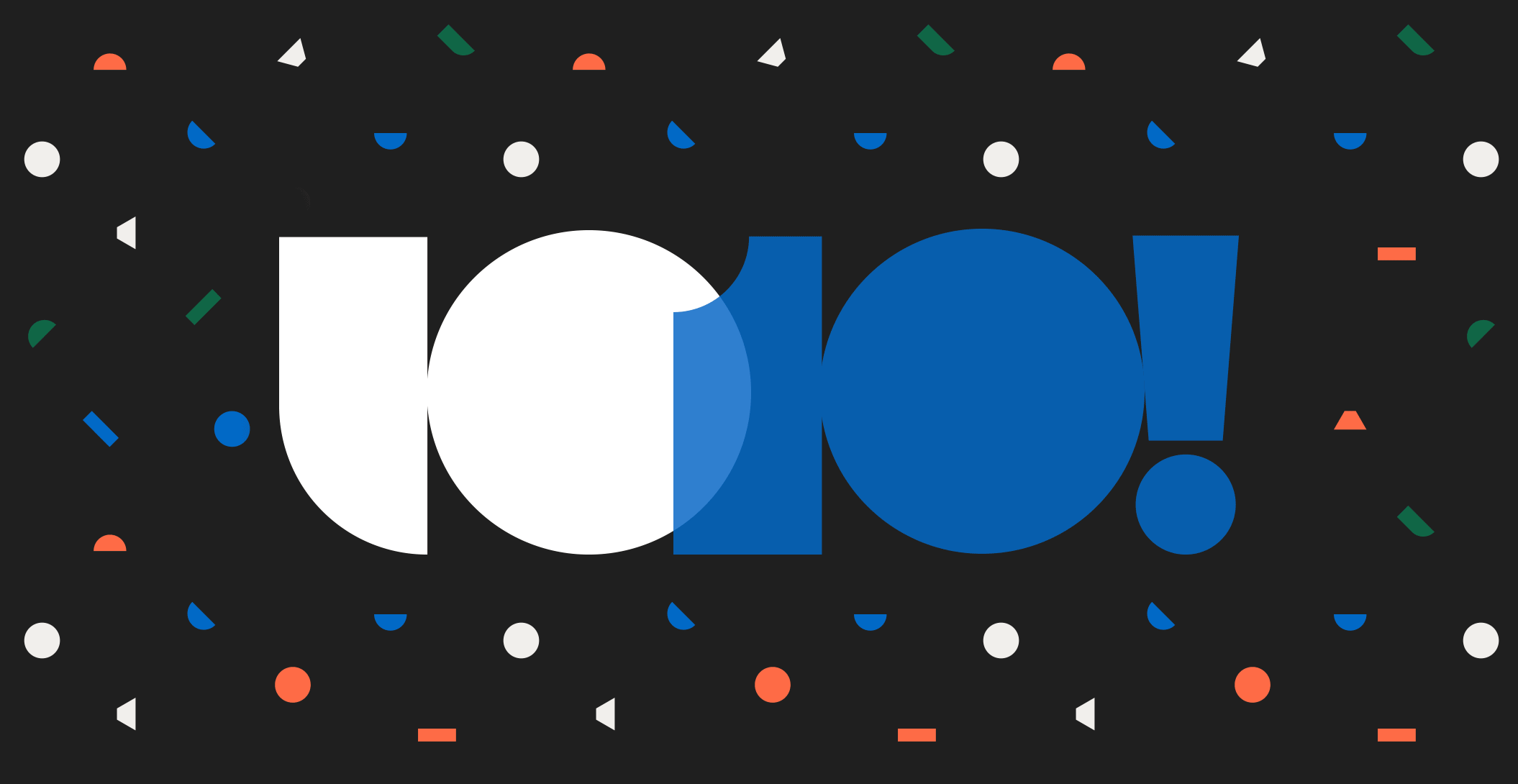
We are celebrating 15 years — and counting — of stories that are deeply researched and deeply felt, that build a historical record of what the city has been.
We are celebrating 15 years — and counting — of stories that are deeply researched and deeply felt, that build a historical record of what the city has been.
To read “What’s in a Gateway” in English, click here.
歡迎點擊此處閱讀這篇文章的繁體中文版本
中文翻译:刘凯仪、杨伯、张坤雅
没有牌坊的唐人街算什么唐人街呢?常被用作划定世界各地唐人街的边界,这些影射着传统中式设计的牌坊无疑与唐人街紧密相连。这个关联部分原因在于文化融合的演变,另部分在于商业营造。在曼哈顿的华埠,牌坊的显着缺少并不是意味着缺少一个拍照的机会,而是意味着数百万美元的社区投资被错过了。最近一次尝试塑造一个呈现出华埠的复杂、不断蜕变的文化和社区的雕塑以失败告终。现在,一项新的计划正在进行,旨在重新设计刘锦中尉广场(Kimlau Square),并在此创建一个「华埠迎客之门」。为了促进社区对话,并阐明关于华埠文化表征的辩论,建筑历史学家和规划师 (Kerri Culhane) 与心目华埠的总监兼创始人邝海音(Yin Kong)共同策划了展览《地方创生与维护- 华埠的人、地方和文化表征》,展览将持续到2024年11月8日。 (心目华埠是纽约市经济发展公司(NYCEDC)的《通达华埠》项目的建筑设计顾问Marvel Architects的社区合作伙伴)。她们在下面探讨了牌坊在过去与现在、居民与游客、文化与商业、象征与刻板印象的交集中的地位。她们认为,只有一种能够调和社区多重维度的过程,才能开辟出一条新的前进道路。
华埠到底在哪里呢?它的定义捉摸不定,因人而异。 不过这块区域总会有些具象或抽象的痕迹,让你感觉到,我已经到了华埠。这里有些建筑带着中式风格的设计,但大多数的公寓楼则为过去一波波移民社区的遗留物。华埠的特色更多地体现在我们如何使用这些空间以及我们在这些空间里如何与彼此互动。这种特色渗透于众多具有文化意义企业的中文标志、公园里的文化及社交活动,以及我们使用人行道的方式:坚尼路(Canal Street)、茂比利街(Mulberry Street)和科西广场(Forsyth Plaza)上那一排排五颜六色的蔬果摊; 勿街(Mott Street)上中式地方特产店里头满溢而出的干货; 格兰街(Grand Street)上阿姨们贩售盆栽、手摘银杏果及粽子。 这些由社区自发实践的地方维护(placekeeping),都展现着由社区共同创造的繁华生态系统。
其他视觉上的线索可能包括公共空间设备的设计,如灯笼形状的街灯,种植竹子的广场和公园。这些被城市规划专家称为地方创生或地方营造(placemaking)的方案,有时是由市政部门根据本地团体或组织的建议来进行。不论是地方创生还是地方维护,每一种方式都为塑造社区的外观、氛围和可识别性起着重要作用。因此,所有人都可以在这块区域获得一种强烈的区域感,无论你是华埠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生活的一部分,还是路过的纽约同胞或游客。
2021 年,在面临着911事件造成经济破坏的第二十年,同时在新冠病毒疫情肆虐的背景下,现任总统将此次疫情归咎于所谓「中国病毒」,由此触发了一系列的反亚暴力事件。正值此时,华埠获得了纽约州政府提供的2,000 万美元的市中心复兴计划(Downtown Revitalization Initiative,DRI)拨款,以投资于「其作为文化目的地的历史,以保护和恢复该社区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市中心区域」。 DRI收到的提案中包括设计建造一座华埠门道, 通过这种地方营造的手段刺激旅游业发展。提案包括了一张援引Wikimedia Commons的照片作为纽约门道的示例,照片拍的是费城华埠的友谊门。这座异彩纷呈的传统拱门由中国大陆在1984年捐赠。这种将费城的拱门复制一份到纽约华埠暗示着一种可互换的无地方性、并给一个充满社区特色,区域感的地方带来可替代的感觉。
纽约市经济发展公司(NYCEDC)负责管理此项多机构、多组织的项目(后来被称为《通达华埠》),故意在信息中没有规定「迎客之门」的外观;他们将聘请一位艺术家,并通过实行社区参与的过程制定设计。尽管如此,「门道」一词具有非常特殊的涵义。 牌坊或牌楼,又称唐人街大门、门道或友谊拱门,源起于神圣的佛教建筑。异彩纷呈、装饰华丽,非常上镜。不难理解为什么它们可以促进一个区域的旅游业,但这些建筑早在 Instagram 和社交媒体出现的几千年前就已伫立于世。这种以印度宗教建筑为基础的古老形式,是如何成为许多华埠的门道的呢?
牌坊,或称牌楼,是中式空间组织的八个主要特征之一, 这种建筑在汉朝(公元前202年-公元220年)中叶,经由丝绸之路与佛教一同从印度传入中国。在中国,牌楼传统意义上的纪念功能与其印度起源类似:将神与非神区隔开来,或是向有社会地位的人士、亲属、学者及遗孀表示敬意。牌坊有地方标记的功能,譬如用于划定北京各区的边界的牌坊。
在 20 世纪的过程中,牌坊的意义发生了变化,从旧金山到新加坡,牌坊变成了唐人街的标志性视觉符号。 搜索「唐人街」相关的图片,你就能在数页的结果中看到五颜六色的牌坊。这些自成一体,装饰华丽的建筑,成为华人聚居区的地标;而在类似华盛顿特区的牌坊,却反衬出了华人社区日渐消散的现象。被人认为中华文化象征的牌坊深受欢迎,甚至被当今的中国重新引回了北京以提升游客的体验。这种现象被Anne-Marie Broudehoux 称为「唐人街化的北京」。 [1]宗教神圣建筑是如何变成了自拍照背景的呢?
三藩市 1906 年后兴建的华埠,其散布着塔的商业区,被认为是北美第一个有意商业化的华埠。在地震和火灾摧毁了原有的社区后,美国华裔企业家围绕「美丽的远东艺术幻想」[2] 重建了三藩市的华埠。他们紧紧接上仅两年前在1904年圣路易斯世界博览会里深受欢迎的中国村。这个中国村在摩天轮和其他有趣的娱乐设施的背景下展示了传统中国建筑。当时面临着要被赶出华埠的危局,本地华人从中国村取得灵感,将建筑环境异域化以吸引白人游客,这使华人得以留在唐人街,并从此建立了游客对其他地方华埠的景观期望。这种巧妙的文化商品化为北美华埠的发展定下了模板,使其成为依赖销售商业化传统的旅游目的地。用历史学家 Mae Ngai 的话,这是 「排华时代美国华人可利用的少数商业活动领域之一」。 [3]
《通达华埠》项目的范围包括一个尚未明确,未设计的「华埠迎客之门」。「迎客」这个词暗示着目标受众是前来华埠的外来者。考虑到华埠被许多不同华裔和亚裔侨民群体认为文化家园,这个门道如何能为他们服务?它能否满足多个群体的需求?这样的门道又应该是什么样的呢?「这个门道是为谁而设?」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更大且更复杂讨论的问题,其核心在于「华埠是为谁存在?」。 如民俗学家 Winston Kyan 所称,华埠处于「个人文化与公共消费文化」[4]的交汇处或模糊边界。它既是华裔侨民及更广泛的亚裔美国社群的经济飞地,也是文化家园,然而其一部分小企业自历史以来严重依赖旅游经济。在它150多年历史的大部分,华埠常常被大众误解为与中国等同的或是一个位于纽约市中心的异域外国殖民地。华埠的「东方化」虽然在美国华裔缺乏经济机会的时代催生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旅游经济,不过也造成了对华埠的普遍误解,这种误解延伸到了任何具有亚洲血统的人。即便是第五代华裔美国人,仍然可能被问到:「你们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每一代对自己的华裔及亚裔美国人身份各有不相同的认识。华埠与整个城市之间的关系和认识也随着岁月的推移而变化。自1965年以来,移民的多样性和人数的增加使得华埠具有细致的区域性特征——从最初以广府移民为主的华埠逐渐扩展至包含更广泛的侨民社群,如今这里每天都有不少于七种汉语及方言被使用。与此同时,随着亚裔美国人群体的日益富裕,华埠经济也正在逐步摆脱对旅游的依赖,以满足此广泛群体的需求。如今,一个强大的区域经济正在为当地居民以及寻求与文化建立更深关系的亚裔侨民提供服务与支持。
孕育了亚裔美国人运动的1960年代的人们,不懈努力争取了历史上缺乏的亚裔群体代表性和可见性,以推翻诸如「模范少数族裔」、陈查理和杂碎等为了让非亚裔美国人更愿意接受而简化的亚裔表现形式。如今,华人侨民社群的代际、阶层和文化多样性挑战着本质化或东方化的文化表现。尽管如此,世界各地的唐人街中仍存在一些熟悉的标志:如牌坊、龙和灯笼。同样标志对我们社群的不同细分群体中具有各异的象征意义——可能引发文化自豪感、被刻板印象化的感觉,或毫无意义。关于牌坊及其他「族裔象征化」的讨论,景观建筑师 Chuo Li 指出:「族裔纪念碑的创建往往会将华埠转变为一个“主题公园”,一个演制文化生产和消费的场所」。[4]在这种说法中,牌坊是为华埠以外的人群所树立的象征,而非为居住和工作于其中的人树立,因而被称为「迎客之门」。社会学家 Jan Lin 指出,「游客注视」对华埠的影响使得华裔美国居民为了满足外来者的偷窥的心理进行适应,并逐渐内化了针对游客的象征。 [5] 门道通常借鉴想象中的历史来迎合这种游客注视;而我们希望看到的地方营造的策略聚焦在确保华埠未来能继续地作为一个充满活力的亚裔美国人文化家园。这种「迎客之门」能如何反映出华埠的社交与文化生活的多样性?它能否帮助维持社区的生机?
整个社区都同意:当华埠作为文化家园的表现和自豪感都至关重要。多数人民心中所渴望的,但无法用城市规划的术语来表达的,即是良好的地方营造与地方守护。然而,在缺乏相关广泛词汇的情况下,牌坊成为了中国文化的速写,往往成为通用的默认选择。我们有机会设计出能服务于华埠的创意公共空间和艺术作品,从而塑造社区群体的叙事,影响其来讲述自身的哪些故事以及影响外界叙述我们的哪些故事。华埠所需的「门道」,一个能够帮助建立跨代的社会与文化联系的门道,可能不会以牌坊的形式呈现而出。
社区参与这个工作是必要的、是充满挑战的,并且几乎总是显得不够充分的。参与公共会议的人群往往是自我选择的群体。现实是,无非进行了多种语言宣传和引导,大多数新移民,尤其是那些刚刚从中国大陆抵达的人,并未参与公共事务。不止缺乏针对新移民们语言上和文化方面的特定宣传,较新的移民也个人缺乏公共事务的经验,繁重的工作和家庭责任往往使他们没有闲暇时间参加公共会议。许多「社区」反馈来自向来参与的积极分子和长期居民们,而他们仅代表华埠和华裔美国社群中的一小部分。有效的参与需要考虑更多视角,这就需要理解复杂的社会环境,并通过多种形式和场所对参与者进行宣传与沟通。真正有意义的参与需要适应的文化能力:不仅用当地的语言和方言,并要设计出一个让人们感到舒适的参与过程。
说了那么多关于门道的话,我们务必反思在纽约修建门道的多次尝试,尽管只有一座成功修成,别的都未有结果。
美国华裔退伍军人忠烈坊(1959-62年)
尽管常常被忽视,纽约市拥有美国唐人街中最早的门道之一,仅次于洛杉矶:美国华裔退伍军人忠烈坊(1959-62年),位于刘锦中尉广场/且林士果广场(Kimlau/Chatham Square)。美国退伍军人会纪念刘锦中尉一二九一分会委托华裔设计师李锦沛(Poy G. Lee, AIA)设计这座牌楼以纪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牺牲的华裔士兵。这一庄严的「新中式」纪念碑履行了牌楼的传统功能:纪念高地位人物。在遵循文化传统的同时,美国华裔退伍军人忠烈坊也反映其时代的现代主义形式,从而成为一项发自华埠社群,并服务于华埠社群的尤为卓越社区纪念碑。 2021年,纽约市将这座牌楼划定为历史文物,成为了纽约市唯一一座反映华裔历史与经历的市立文物。
然而李设计师其实设计了两份方案。最初的设计是一个宏伟、传统精美的牌楼,中文媒体描述其方案为「美丽」和「精描细绘」。[6] 由于担心华丽的牌楼将在繁忙的且林士果广场(Chatham Square)中吸引太多游客,并分散司机注意力,李设计师被要求制作一个简化版——一个显然不是用于吸引游客的版本。于是,李设计师的诠释采用了此形式的神圣意义,再加上其时代的风格, 从而设计了一座纪念并弘扬社区的一段重要历史的牌楼。
纽约华埠的门道 (1982, 2006, 2016-19年)
虽然纽约华埠是美国唯一一个没有刻板化的牌坊式门道的大型华人社区,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努力争取过。 1982年,华埠领袖们提出了一项由广东工程师兼设计师何铁基(Ho Tieh-Chi )(1937年-)设计的20×40英尺的精美华埠门楼方案,被市政府正式驳回。 2005年-2006年,纽约市议会向华埠的社群及商业团体提供配套资金,以助建起「一座以混凝土与花岗岩门楼,以象征华埠的入口」。香港出生的 Peter Poon 建筑师设计了这个方案,其设想是要横跨坚尼路(Canal Street),然而市交通局(DOT)拒绝提供相应许可证。
最近一次尝试建造门道应对所有参与当前的努力的人被视为一篇警示故事。2016年,交通局(DOT)与 Van Alen Institute 和华埠共同发展机构(CPLDC)合作,使用了911事件后划拨于经济复兴的资金,发起了《唐人街之道》门道设计竞赛,吸引竞标。此项目的设计大纲从本地社群中征询极少意见,却共收到80多份来自世界各地艺术家及设计师的投标。这些投标中包括了各种刻板元素诸如筷子、美式中餐外卖盒、灯笼、月亮门等,同时也有几份现代设计感的牌坊。 (为了全面起见,作者们也提交了一份投标。该投标没有针对推出任何特定的设计,而是围绕着一个社区参与的方案。)华埠公众没有任何机会查看或对80多份参赛作品发表意见;他们只能查看少许设计师自愿公布的那些竞标,而且只有在线搜索时才能查到。
《龙吟》,由纽约公司 LEVENBETTS与 UAP 以及澳大利亚籍华裔艺术家李林迪(Lindy Lee)共同设计的方案,最终以匿名评选委员会被选为中标方案。其「门道」主体抽象,伫立在细细的柱子上,由金属圆柱体不规则地堆叠而成,并且设计了圆柱体有如瑞士芝士般的孔洞。投标方称他们从苗族鼓楼那里获取灵感,然而这种文化渊源却与纽约华埠的移民史并无直接联系。
中标的提案由一个完全白人的设计团队向第三社区委员会的交通小组委员会介绍提案。华埠社群的成员提出了诸多异议:设计并没有考虑到风水(作品的孔洞将社区的财运溜走)、设计未能捕捉纽约华埠的「真实」地气、有些成员希望看到更加传统的元素(龙、凤、塔),有些则希望完全超越传统(不包含金色、红色,不包含龙)、设计与华埠居民并无关系,并不能起到实质作用、方案并没有能通过设计带动解决坚尼路(Canal Street)的行人及行车交通问题。虽然区民在社区会议中以多种原因反对了中标的方案,然而参与者没有对华埠门道的应当设计达成一致。
面对着社区的反对,交通局撤回了该项目。虽然这无疑让付出心血的设计师感到失望,但更令人失望的是华埠失去了数百万美元的投资。如果从一开始就让社区参与对话,并进行具有适应语言能力和文化的交流,那么一个满足社区需求的门道项目或许已经在修建中了。
正如一个迎客之门划定内与外、唐人街与城市之间的边界,它也将这些地方连接在一起。实行迎客之门是一个弥合老一代、年轻一代、以及侨民各个角落之间的文化鸿沟的起点,从而让我们组织社区的宗旨不仅仅基于我们的复杂且常被误解或抨击的历史,而是我们共同的未来。华埠迎客之门将对纽约华埠的认知产生世代影响。我们不对这个新门道假设任何形式——甚至它应否形成实物的形式我们都没有断定结论——而是相信信息共享和深入倾听的过程能够激发并为社区带来一个适当的结果。
Anne-Marie Broudehoux, “The Chinatownization of Beijing: Urban Renewal and the Commodification of Identity,” conference abstract from “Identity, Tradition and Built Form: The Role of Culture in Development and Planning: Fif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December 14-17, 1996, Berkeley, California: Traditional Dwellings and Settlements Review, Vol. 8, No. 1 (Fall 1996), 58.
Look Tin Eli, “Our Oriental City,” (1910), quoted in Philip P. Choy, The Architecture of San Francisco Chinatown (San Francisco: Chinese Historical Society, 2008), 18.
Mae M. Ngai, “Transnationalism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Other’: Response to the Presidential Address,” American Quarterly, Vol. 57, No. 1 (March 2005): 59-65.
Chuo Li, “Chinatown and Urban Redevelopment: A Spatial Narrative of Race, Identity, and Urban Politics 1950–2000,”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2011: 214.
Jan Lin. Reconstructing Chinatown: Ethnic Enclaves and Global Chang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8: 172.
联合日报 (United Journal), May 1961.
The views expressed here are those of the authors only and do not reflect the position of The Architectural League of New Yor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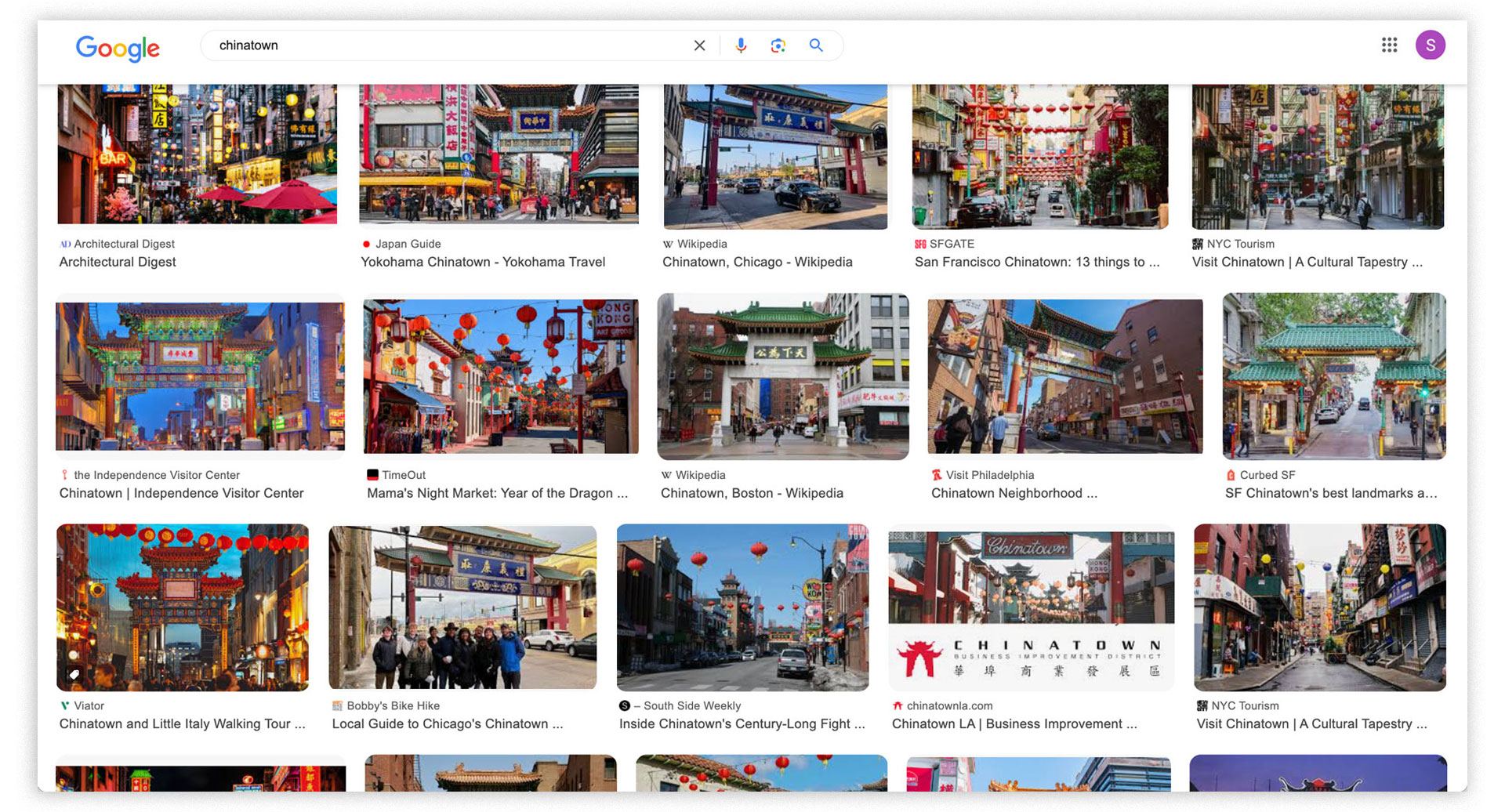
![[左图] 公元1世纪的托拉纳门,位于印度中央邦桑吉窣堵坡。Leon Meerson 摄影,取自 <a href=https://www.flickr.com/photos/lenchik/116887771/in/photostream/>Flickr</a>。](https://urbanomnibus.net/wp-content/uploads/sites/2/2024/10/07_116887771_9df620592f_o-1.jpg)
![[右图] 在陕西一座汉朝立的牌楼展现了中国最早对于托拉纳门的一种诠释。俄罗斯前往中国的科学商业远征,1874-75年。照片取自 <a href=https://www.loc.gov/%20%20item/2021669674/>Library of Congress</a>。](https://urbanomnibus.net/wp-content/uploads/sites/2/2024/10/08_116887771_9df620592f_o-1.jpg)
![[左图] 中国展馆入口,百年世博会,费城 (1876年)。照片取自 <a href=https://libwww.freelibrary.org/digital/item/1007>Free Library of Philadelphia</a>。](https://urbanomnibus.net/wp-content/uploads/sites/2/2024/10/09_large-1.jpg)
![[右图] 中国村,圣路易斯世界博览会的官方纪念品,1904年。图案取自 <a href=https://mohistory.org/collections/item/N20408>Missouri Historical Society</a>。](https://urbanomnibus.net/wp-content/uploads/sites/2/2024/10/10_default-e1727873311680-1.jpg)



